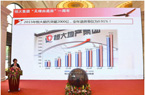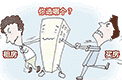零星管制
(20世纪初期以前)
19世纪中叶前,欧美国家很少对私人的土地利用进行管制,土地所有权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所有权人拥有排除他人干涉土地的完全权利。政府对土地利用的管制仅限于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不能给他人或邻居造成损害。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世界各地的城市迅速形成并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市内住宅出现不足,平价住宅大量兴建。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计划和管理,许多城市开始出现住宅拥挤、环境脏乱、贫民窟蔓延等问题。即使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的城郊,由于道路设施的不齐备和对“建筑自由”的尊重,住宅建筑显得毫无秩序。在此背景下,出于对安全、卫生、道德的考虑,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规范私人的用地行为,特别是对住宅用地的使用进行规范,重点是对基本的道路线、建筑线进行管制或针对个别地块进行零星管制。
针对道路线和建筑线进行管制
19世纪中叶,德国国内开始意识到应该对土地的所有权加以限制,以保障市民良好的居住环境,因此产生了应制定土地利用“周详计划”的观念,开始对基本的道路线和建筑线进行管制。所谓道路线是指各地区内道路的位置,建筑线是指各地区内建筑物的位置。这种管理制度成为了德国地方政府都市计划的基本要求。
英国、日本早期出于改善居住环境、公共卫生和道路布置的原因,均开始拟定最初的建筑管理法规或土地使用规划方案。比如1858年英国制定地方政府法案,授权地方政府制定建筑管理法规;1888年,日本发布了《东京市区改正条例》,拟定了以建筑物为主的都市计划。
针对个别地块进行零星管制
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以保护毗邻地区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为目的,针对个别地块进行零星管制,比如要求一些殖民村的火药生产和贮藏必须远离住宅与商业区。马萨诸塞州湾的一个法令还禁止家禽在小岛上过度吃草,以保护当地的草地和灌木,防止给公众造成损害。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零星管制只针对某些妨碍公共或他人利益的特殊问题,或是简单地指定部分地区的道路线和建筑线,并没有覆盖整个城市范围。对公众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也容易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但在管制的性质上,由于多数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在实施时有很大的局限性,只短暂地满足了当时城市部分地区发展的需要。
严格管制
(20世纪前期至中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工业污染使城市环境急剧恶化,工业生产的负外部性进一步凸显,出现大量与居住、商业活动相冲突的现象,影响了城市土地整体的最高最佳使用。但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土地私有制,因此地方政府无法对土地利用作出过多干涉。在此背景下,出于对城市整体环境与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开始限制土地的开发,即试图通过政府管制来消除因土地混合利用带来的负外部性,纠正“市场失灵”。
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拟订并通过了《雅典宪章》,该宪章提出,工业污染、城市拥挤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缺乏分区规划造成的,而通过把城市分为居住、工作、休憩和交通四类功能区,并结合现有的交通和建筑技术可以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实现城市的有序发展。该宪章对全面推行严格分区管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简单实行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制度,是指将管制范围内的土地,依使用目的与需要的不同,划定为各种不同的使用分区(如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各分区再视需要,依使用强度的不同,划设若干细分的使用区,并限制有妨碍各分区用途的其他使用。其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编绘土地使用分区图,指派各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区位;二是制定管制规则,规范各种分区的建筑行为与活动行为。
1916年,第一个土地分区管制条例在美国纽约通过,并以治安权为依据,规范建筑物的密度、高度、容积率与空地面积等,规范土地作为住宅、工业、商业或其他目的的使用。此后,分区管制条例在全美范围大量出现。192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欧几里得案中作出判决,认为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是一种维护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道德与公共福利的治安权,确定了分区管制的合宪性。1928年,美国发布了《城市规划标准授权法案》,为各州和地方政府制定分区管制条例奠定了法律基础,但该法案未对规划与分区管制制度做明确的界定,使得美国许多城市只采用了分区管制制度,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划作为基础。美国这个时期的土地使用管制是僵化没有弹性的,排外性的分区管制便是典型代表。
在规划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分区管制与美国不同,德国擅长统一的规划管理,其对土地用途的管制通过在规划基础上实行分区管制实现。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德国的规划体系自上而下包括覆盖全国的“国土计划”、超越地方政府范围的“空间计划”,以及从基本道路线和建筑线发展起来的地方政府的“都市计划”。都市计划的核心是建设指导规划制度,主要对市镇内的土地建设和使用进行准备和引导,其又分为准备性建设指导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约束性建设指导规划(营建规划)两类。土地利用规划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对整个市镇内的土地框架性地确定预计的土地用途,营建规划则确定了市镇部分土地可用于建设,并且明确了土地使用的种类和规模。
日本参照德国,在该时期也采用在规划基础上实施分区管制的方法。1919年,日本公布了《都市计划法》,按照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理念,将城市划分为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确定了最初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在规划的基础上实行开发许可制
这一时期,英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则更进一步,实现了从土地用途分区管制向开发许可制的转变。1909年,英国颁布了《住宅与城市规划法》,该法授权地方政府拟定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并对将要或可能要开发地区的土地实施分区管制,以确保土地的布局和利用能符合卫生、舒适和便利的要求。到了1947年,英国重新修订并公布了《城乡规划法》,建立起了英国现代城乡规划制度,确立了发展权国有制度和开发许可制,强调所有土地均需纳入计划管制,任何开发行为均需事先获得地方规划部门的许可。由此,开发控制和规划控制成为英国城乡规划体系中的重要元素。
总体来说,严格的用途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隔离了不兼容的土地、减少了工业污染对居住环境、商业办公等活动的影响,通过牺牲小部分人的私利来增进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大大改善了城市以往杂乱无序的面貌。但其也产生了一些弊病:一是造成城市空间结构及活动的过于单调。二是妨害了市场竞争,造成社会不公平。三是造成了社会的隔离。四是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因此,虽然传统严格管制的目标是美好的,但事实证明它并没有实现预期效果,也无法继续对城市发展作积极的引导。
弹性管制
(20世纪中后期)
对传统土地分区管制的改良和创新逐渐兴起。1977年出台的《马丘比丘宪章》在《雅典宪章》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该宪章认为,城市职能是多样的,需要用整体性的思维来分析;城市规划是动态的,需要突破把规划作为静态终极蓝图的传统观念,应进行过程性规划。一味地强调分区,会忽略城市的有机组成,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交往,使城市失去生机和活力。《马丘比丘宪章》为世界各国陆续采用弹性化的用途管制制度提供了依据。
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各种弹性管制措施,比较典型的有英国的规划协议及精简规划分区、美国的弹性分区管制、日本的分区管制与开发许可制并重、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在特定区域内实行土地用途弹性变更制度等。
实行规划协议及精简规划分区制
在土地用途弹性管制的多种手段中,开发许可制基础上的规划协议制在英国备受推崇。由于严格管制阶段建立起来的开发许可制要求所有的开发行为前均须申请规划许可,在许可过程中,规划是实质性的考量依据,规划部门会严格按照规划来授予或拒绝规划许可。除了取得规划许可外,开发土地还需要缴纳100%的“开发捐”。这些前提条件严重地妨碍了英国土地开发和城市发展的活力。因此,为增加规划许可的弹性,地方政府开始引入规划协议,即由土地开发者与地方政府协议确定土地开发许可的有关权益,这个协议可能是要求开发商开发土地时附带配建公共设施,可能是限制土地的开发或使用,也可能是要求开发商给地方政府一笔钱。具体必须在地方政府和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执行,这种方式的引入给予地方规划部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大大增加了用途管制的弹性。
此后,为了解决诸如“内城退化”、开发许可制的审议拖延、效率低下等问题,198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住宅及规划法》确立精简规划分区制。精简规划分区是指在指定区域内直接予以规划许可的一种管制方式,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针对特别的开发项目,在详细展列后直接予以开发许可,其他开发行为仍遵循正常程序;二是广泛地授予开发许可,只针对少数的、特别的项目采取开发管制。精简规划分区使得经济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实行弹性分区管制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越来越重视规划的制定,对土地使用的介入有强化的趋势。但分区管制制度在美国仍然流行,并逐步引入弹性分区管制的手段。这个时期,美国各地的管制工具在传统严格分区管制中增加了环境管理(划定敏感区、特别保护区等)。
60年代后期,管制的目标除了实质和环境层面外更增加了社会和经济层面,管制工具更趋多样,如采用浮动式分区、契约式分区和土地开发权转移等。具体来说,浮动式分区是指土地规划时,不事先划定全部的分区界限,而是只将有把握的地方先行划定,待时机成熟时,配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再作变动性的划定。契约式分区是指分区管制在法律上有限制性,契约期满就可以变更不合时宜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开发权转移是指将受控制的土地开发权通过开发权买卖市场转移给他人或转移至其他土地的行为。70年代起,美国地方政府开始逐步结合英国开发许可制的精神,将规划协议的方式引入土地用途管制。
8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在土地用途管制方面由直接介入逐步转变成引导角色,市场则发挥主要作用,公私合营的管理模式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比如,在公私合营组织的操作下,弃置的港口和荒芜的工业区重新被作为住宅、办公、游憩用地使用。这个时期美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呈现管制工具愈趋多样,规划重视协商程序,规划的角色更多元等趋势。
同时实行土地分区管与开发许可制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也参考英国开发许可制的精神,对土地用途管制实行分区管制与开发许可制并重的方法。一方面,在严格管制阶段的基础上,通过重新修订《都市计划法》,进一步完善全国性的规划体系,把城市土地划区分为市街化区域和市街化调整区,并进一步决定功能区和用途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城市。另一方面,在土地分区管制中引入开发许可制,要求市街化区域内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开发行为均需申请开发许可;而市街化调整区域,原则上禁止开发,以此来确保都市土地利用的秩序及环境品质。
此外,日本设置了特定街区制,它类似于美国的开发权转移,在被指定的街区之间允许容积率的转移,以此推进城市再开发,也增加了分区管制的弹性。总体来说,日本的土地利用管制效仿德国,相较于英美,弹性管制的力度不大。
在特定区域内实行土地用途弹性变更
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弹性管制措施在土地用途变更管理方面较上述国家有了更大的突破,即在特定区域允许土地的混合利用或一定比例的用途变更弹性。如新加坡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允许在“白色地带”和“商务地带”内,随时变更土地用途,更好地适应市场需要。“白色地带”计划规定,在政府划定的特定地块,允许包括商业、居住、旅馆业或其他无污染用途的项目在该地带内混合发展,发展商也可以改变混合的比例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在项目周期内改变用途时,无须交纳额外费用。“商务地带”是指将园区内原工业、电信和市政设施用途的地带重新规划为新的商务地带,是“以影响为基础”的规划方式,允许商务落户于不同用途的建筑内,改变用途无须重新申请,并且同一栋建筑内也允许具有不同的用途,以增加土地用途变更的灵活性。
本世纪初,我国台湾地区公布了《工业区用地变更规划办法》,其核心思想是增加工业区内土地使用的弹性和规划调整的适应性。具体来说,为促进产业升级,允许工业区内的土地有一定比例的用途变更弹性。比如,工业区内原生产事业用地可以变更为相关产业用地,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餐饮、通信、工商服务、社会与个人服务、金融、保险,以及不动产业使用。但是,用途变更的比例受到严格控制,规定生产事业用地所占面积,不得低于全区土地总面积扣除公共设施用地后的50%;社区用地不得超过全区土地总面积10%;公共设施用地不得低于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0%;相关产业用地不得超过全区土地总面积扣除前二款公共设施用地及社区用地面积后的50%。
以上措施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局部土地用途的弹性,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